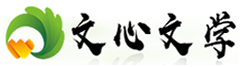故乡的血脉[ ]
在故乡的原野上,沟渠像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织线,把那些大的小的、圆的方的藕塘、油菜地、秧田连起来,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清晨,东方刚显鱼肚白,鸟儿在令人心醉的空气中欢叫不止,露珠在草尖上颤动,青苔愉快地闪着绿光。女人们提着装满衣服的水桶,走向村庄的沟塘,水面上先是响起单调的极其细微的“
嘭嘭”的槌衣声,随后,男人们来到沟塘边,将一只只空桶“蓬蓬”地甩入水中,等桶全部沉入水后,再慢慢地提起,直到装满,“哗”的一声提起来。渐次地,“唰唰唰”的洗衣声,提起带水衣服的“哗哗”声,笑声,闹声响成一片。各种声响在沟塘上空汇成一支清新又和谐的乡村协奏曲,从村头飘到村尾。那声音湿湿的、润润的,那是水乡独有的旋律。
沟里的水叮叮咚咚地流着,像多情的少女哼着婉转美妙的歌,惹得一群群小鱼细虾在水中嬉戏追逐,让水沟生动起来;鳖欢快地从塘里爬上岸来晾晒它们的盔甲,一如隐士晾晒古老的经书……令人忍不住停下匆忙的脚步,上前瞧瞧,凑凑热闹。鱼虾龟鳖生性胆怯、多疑、机警,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它们便闪电般地逃走了。
沟里产卵的鱼逆水上行,水就慢慢送它们一程;塘里扎猛子的鸭让水必须画圆一个个漩涡,也搅了绿水的好梦;路过水沟的小牛贪恋水的清凉,躺在水里泡澡,尾巴一动,就系住一朵朵浪花;塘边歇息的庄稼人把脚伸进水里,水就清悠悠的摩挲着他们那粗糙的皮肤,还捧起沙粒轻轻按摩那结满老茧的脚底……水的流速缓慢,它不急于带走太多的东西,而是让掉进水里的一切,比如雪、雨水、落叶或少女的头饰,都有沉淀和重新上岸的机会。
沟塘两岸,正直的、弯曲的、高接云天的大树和不思进取的灌木、野草,纷然杂陈,互相衬托,把沟塘两岸染得碧绿,装扮得像是要出嫁的新娘。沟塘里的水草,被水推着、摇着,悠闲地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舒展着轻软的胳膊。偶有几朵小花飘落水面,微波就拥着那落花,一荡一漾,于是,整条沟、整口塘都弥散着花的馨香。
沟塘边,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唱着歌,那清脆的叫声仿佛天籁;鸡欢快地在草丛里寻找虫子,偶尔哼上几声;活泼的小燕子时而低飞,时而又高高地飘向天空,时而成双齐飞,时而又成群而来,它们像勤勉的保安,来来回回逡巡着;辛勤的蜜蜂扇动着不知疲倦的翅膀在花丛中起舞,准备为人类酿造上等的蜂蜜……
农忙时节,庄稼人摇着古老的水车,沟沟塘塘里的水便随着那悠扬的吱呀声,汩汩流进农田,滋润着村庄里的农作物,支撑起小村的希望。稻田里的水涨涨落落,这是田野由黄而绿的呼吸;芋田里的水起起伏伏,那是芋头苗成长的资本……
庄稼人在稻田里忙一阵子,会在沟埂塘堤上休息一会。届时,他们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洗净手,坐到树荫下,掏出一支烟来,点上火,一边吸,一边满足地看着水里打着滚的鱼儿。待烟抽完,聊几句,又继续下田干活。沟埂塘堤就像是庄稼人在稻田里征战的休息室,但他们只会小憩,绝不久留。
传说那绿墨墨的沟塘深处潜藏着一些鬼怪,我对此一直存在恐惧,不敢独自踏入沟塘半步。但炎热的夏天,我和童年伙伴经常去沟塘边割草,为生产队的牛准备粮食,累了,走向沟塘深处,走进它们的身体里,水“嗖”地一下抱紧我,湿漉漉地贴上来,有久别重逢的急切。水不深,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照样可在沟塘中玩耍,既消暑又可以娱乐。
故乡的沟沟塘塘,就像一条条血脉,布在大地母亲的身上,浇灌着大地上的水田、旱地、菜园,滋润着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乡儿女。它们是小村生命延续的源泉,支撑着土地上的儿女繁衍生息,代代生生无穷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