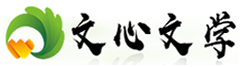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闯荡在都市边缘》第001章[ 青藤文学社 ]
导读:在苏浩八岁那年娘就撒手而去了,从此他变得寡语少言不爱吭声,村里人看到这个没娘的孩子自然多了几分同情。 在苏浩的记忆里娘性情温和慈祥处处惯着他,尽管家境不好倒也把他拾掇得干净利落,冬天哼着小曲哄他入睡 ...
第001章 懵懂无知闹笑话 坎坷波折多磨难
在苏浩八岁那年娘就撒手而去了,从此他变得寡语少言不爱吭声,村里人看到这个没娘的孩子自然多了几分同情。
在苏浩八岁那年娘就撒手而去了,从此他变得寡语少言不爱吭声,村里人看到这个没娘的孩子自然多了几分同情。
在苏浩的记忆里娘性情温和慈祥处处惯着他,尽管家境不好倒也把他拾掇得干净利落,冬天哼着小曲哄他入睡,夏天拿着蒲扇给他驱蚊扇风。随着娘的去世这些温暖的画面只能珍藏在记忆里,难受委屈的时候想起娘的慈爱只能暗自落泪。
从他记事起娘就病怏怏弱不禁风,仿佛一阵风吹过来就能把她卷到天上去,厨房的犄角旮旯放着煎药的瓶瓶罐罐,破屋里总是弥漫着中草药刺鼻难闻的味道。
苏浩是家里的老幺,在他之前娘给他爹苏成耀生过两个孩子,头一个男娃还没等家里人高兴多久就夭折了,娘哭得差点背过气去。次日早上天色未亮,邻居孙茂才从他爹手里接过裹好新衣身子早已冰凉的孩子,趁着月色悄无声息把这个早夭的孩子卷了一张草席在外面埋了,具体埋在哪里谁也不过问,村里对于早夭的孩子向来都是这般处理的,以免睹物伤情。
姐姐苏璇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一丝欣慰,娘的病情似有好转的迹象,可等到生下苏浩以后她的身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天夜里,娘的一声颤抖尖叫把他爹苏成耀吓得不轻,只见她目光恍惚游移躲闪身子不停的颤抖,眼里满是惊惧的看着空洞屋梁,嘴里不断重复着:“鬼,有鬼……”然后抱着他爹的身子哆嗦的如同筛糠一般。
他爹瞅着这间破旧老屋的屋梁空空如也,但看她瞪着惊恐的眼睛惊吓过度的样子,恍惚中倒真感觉有个模糊的东西坐在屋梁上面目狰狞的看着他,顿感头皮发麻,一阵寒意从脚底油然而生,想起以前在这屋吊死的那位长辈,暗自琢磨难不成是他老人家?于是赶紧跪在地上恭敬虔诚地对着空洞的屋梁说:“老根叔,我明儿一准给你烧纸,你就别吓娃他娘了,她那身子骨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呀……”这么说着就磕起头来,惊奇的是不多会儿,娘终于不再哆嗦了。
待到天明,爷爷茂朴老汉得知情况,叹息了一声说:“你茂根叔当年被姚天德这个狗日的害死的,心里憋着怨气吧,咋这么多年了还不消停倒出来吓自家人了?”
这时小辈们才知道文革时苏家的一个长辈想不开在那间老屋上吊自杀了,大人们怕吓着娃娃从未提及此事,时隔多年,大家似乎忘记了当年那件不愉快的往事了。
茂朴老汉当机立断对他爹说:“去把娃儿舅妈请来看看吧,这么闹腾还不把两个娃娃吓出个好歹来?”
苏浩舅妈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仙姑,在农村仙姑是份受人尊重的职业,谁家娃娃撞邪遇鬼医院诊治不了的,大人们就提着礼物陪着笑脸说着好话求到舅妈的门上了。对于她来说别人能登门相求说明人家看得起自己,这个时候万万不敢怠慢求访之人,就算再忙也要放下手里的活儿随人去瞧病。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过也有瞧不好的时候,瞧好病的人家必定感恩戴德,没瞧好的也不敢有半句怨言,一向以来迷信的山里人总觉得仙姑神汉们神灵附体,认为他们身上有着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能驱鬼唤神撒豆成兵,有通天之能谁也不敢得罪。
他爹苏成耀匆匆赶过去说了家里闹鬼的经过,舅妈听完就收拾做法用具随即赶了过来。到了以后就吩咐摆桌子设好香案,然后在装满粮食的瓷碗里插上几柱香燃起,她做法的过程和别的仙姑神汉大同小异,只见她从包里拉出一块丝帕红巾戴在头上,又把丈余红绸系于腰间,手拿桃木剑围着娘绕了几绕,嘴里念念有词挥着桃木剑指东打西、手足舞蹈起来,不大一会儿,就见她大汗淋漓像得了羊癫疯似的很有节奏感的一阵哆嗦。
接着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突然从她嘴里冒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诉说冤屈,不过年老的左邻右舍听出是那位屈死长辈的声音,然后亲人们通过舅妈与死去的长辈开始对话,这位屈死的长辈说了一堆他生前的琐事,而那些事发生的时间舅妈肯定是不知道的,可此刻却偏偏从她嘴里说了出来,大家眼神交汇惊骇不已。
舅妈做法的过程中所有人屏声静气连大气都不敢出,平时调皮捣蛋的娃娃们看人们神情肃然也乖乖躲在大人的怀里,瞪着眼睛好奇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敢吭声,生怕惊扰了鬼神。
人鬼对话过程差不多持续了10多分钟,屈死的长辈诉说了一番冤屈后,又抱怨自己住的地方阴冷潮湿,把活着的亲人们听得一个个哭眼抹泪。做法接近尾声时,舅妈大喊一声‘着’桃木剑在土坯的地面上划出一道弧形,然后端起桌上的白开水喝了一口喷洒出去,作法完毕后她瘫痪在地整个人跟虚脱了一般。
“拿点白石灰来。”舅妈歇息片刻后吩咐了一声,大家不知道白石灰有何用途,可谁也不敢多问,赶紧把白石灰找来。舅妈念念有词抓着石灰沿着房子周围撒了一圈,一切布置妥当后对家里人说:“有空去把他的坟修一下,他在那边住不好可不得跟你们折腾嘛。”
果不其然,等亲人们去修葺坟地的时候才发现墓地周边不知什么时候有了一片湿地,迁坟以后娘就再也没有看到脏东西了,可经过上次的惊吓她的精神一直没恢复元气,趋渐消瘦。
一天半夜姐姐苏璇突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山里离村大队的卫生室路途较远,大半夜赶去也找不到医生,第一个男娃早夭的阴影让家里人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煎熬到天色微亮,爹就抱着身子滚烫的苏璇火急火燎往村卫生室赶。娘身子骨弱走路一步三喘,只能心急如焚在院侧磨盘旁的老桃树下向山下张望着,等待着。。。。。。
直到下午,爹才神情萎靡耷拉脑袋哭丧着脸一个人回来了,不用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娘还是不甘心的抓着爹的身子摇晃着、哭叫着:“他爹,璇儿呢?”
“送的太晚了,来不及了。”爹说着一屁股蹲在地上,用手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揉搓着,耷拉着脑袋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一时老泪纵横,眼泪透过捂着脸的手指缝隙清晰可见,吧嗒吧嗒直往地上砸。突来的噩耗让娘再也支撑不住,身子挣扎的晃了几晃就瘫软在地,爹见状赶紧站起来扶着她叫道:“他娘……”
姐姐苏璇乖巧可爱、聪明伶俐,她的夭逝再次让娘体会了丧子之痛,苏浩看娘悲痛欲绝的样子也躲在角落里流泪不止。
不一会儿,闻讯而来的左邻右舍围满了屋子,只见娘气若游丝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没有一丝光泽,头胎男娃的早夭让她措手不及,苏璇的夭逝更是把她打击的彻底崩溃。
看着娘油尽灯枯的憔悴模样,大老远请来的医生悄悄把爹拉到一边,摇了摇头表达了他的无能为力,叹了口气说:“早点准备后事吧。”
苏浩清楚的记得娘走那天的情形,当时他趴在娘的怀里不住的抽泣,娘看他这么小心中不舍,挣着虚弱的身子对他爹说:“成耀,你可要照顾好浩娃子……”然后看着小苏浩眼里满是慈爱,不舍抚摸着他的头说:“我可怜的浩娃呀,你可咋办呀?”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瞳孔的亮光随即消失不见,只听‘咯’的一声就此气绝,顿时一屋人抽泣声此起彼伏,苏浩抱着娘的身子嚎啕不止,一旁的婶子见状赶紧把他抱开。
娘出殡那天,家里人听从舅妈的吩咐用红绳把苏浩栓到磨盘上,据说这样可以防止神鬼附体,然后大人们开始忙活下葬事宜,他满脸泪痕在磨盘上越想越难过,不管不顾解开绳子跑到墓地哭得惨不忍睹。他这一哭墓地大婶大妈们也跟着哭得稀里哗啦,舅妈见状吩咐大婶把他抱走,大婶抱他的时候,他挣扎的踢掉了脚上的鞋子。
安葬好娘以后家里冷清了好一阵子,村里的婶子们看他爹一个人忙里忙外准备再给他张罗个女人过日子,他爹婉拒说:“不找了,我把浩娃子养大就好了,我就他一个娃了,要是让他受点啥委屈就对不起他死去的娘了。”大家见他坚持只好作罢。
亲眼目睹娘的去世让苏浩终身难忘,每当伤心难过的时候总会想起娘那张温暖慈祥的脸,就像电影画面一般一帧一帧的在脑海里萦绕,直到二婶嫁到苏家以后才让他感到有了母爱般的呵护。
二婶冯雅玲在苏浩鼻涕虫满脸爬的时候就嫁给了二叔,那时的山野粗妇还没有戴奶罩的习惯,走起路来两个肉球在胸前荡来荡去极不雅观,可二婶总是穿戴的整整齐齐,收拾的利利索索宛如画中仙子。小的时候苏浩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老议论说二婶是个破鞋,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嫁给大她十多岁老实粗鄙的二叔。
二婶对苏浩特别疼爱,每次去镇上赶集的时候总是给他买大白兔奶糖,吃到嘴里甜丝丝的,他舍不得一整块吃掉,一点点舔着奶糖让糖水顺着喉咙慢慢滑进去。就这样苏浩对二婶有了依赖,二婶去忙活的时候他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后面,以至于后来他有了一个不雅的外号——‘牛蒙眼’。
一次二婶领着他去洗衣裳,到了井边一堆老娘们叽叽喳喳说着扯淡的闲话,苏浩乖巧的蹲在旁边的石板上闷不吭声,当二婶洗奶罩的时候,苏浩没见过这个新奇玩意是个啥,就蠢萌的问:“二婶,你洗的是啥?”
二婶看着旁边洗衣裳的婆娘们尴尬的不知怎么回答,这时一个堂嫂插话道:“浩娃子,你婶洗的是牛蒙眼(拉磨的时候防止牛偷吃磨盘上的粮食,给牛遮一个眼罩叫牛蒙眼)。”可是懵懂无知的苏浩不知道人家在拿他取笑逗乐,有些似懂非懂还是忍不住有些好奇,抱着不耻下问的精神接着问:“牛蒙眼干啥子要洗哩?”
洗衣裳的婆娘们再也忍不住一起夸张的笑得前俯后仰,二婶看她们笑岔气的样子哭笑不得,冲她们说:“小浩还是个娃娃哩,你们是咋当长辈的,咋和他开这样的玩笑嘛?”虽说苏浩不懂这帮婆娘为啥会笑成这个德行,可看她们笑得如此淫荡浮夸这才隐约感觉被戏弄了,窘迫的脸色通红赶紧溜之大吉。
于是‘牛蒙眼’顺理成章也就成了苏浩的外号,面对着这些长辈们的调侃取笑他总是无可奈何,只能躲远点免得惹上一身骚,自此以后在他心理留下了阴影,以至于后来看到女人们晾晒的奶罩总是让他想起那个令他难堪的笑话。
尽管如此,苏浩还是像往常一样黏着二婶,更容不得别人对她说三道四,一次放学回来的路上,一帮熊孩子又嬉笑着说二婶是个破鞋,让他感到受了莫大的羞辱,抓起一块石头砸了魏二黑的娃子小黑子一脸血。
后来魏二黑带着小黑子来找他爹苏成耀讨公道,他爹不管三七二十一怒不可歇拿着编筐子的柳条一下接一下的往他屁股上抽打着,苏浩为了二婶的名声任由他爹生生的把一根柳条抽断,咬牙忍泪倔强的一声不吭。
“这是咋了嘛,把小浩往死里打。”二婶挑着水桶还没走到院子里就听到柳条抽在身上的啪啪声,撂下水桶跑过来把苏浩抱起来,扒下裤子看他屁股上的一道道伤痕责怪他爹下手太重,苏浩见到二婶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发泄着心中压抑的委屈。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他已不再懵懂,终于明白了以二婶这般模样为什么会嫁给武大郎式的二叔了,在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中他得知了二婶不幸的遭遇。
二婶冯雅玲是十多里外冯家铺子冯雪庆的闺女,小时就是个美人坯子,圆润的鹅蛋脸白里透红,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像两颗黑葡萄一样衔在眼眶里。随着慢慢长大越发招人疼爱,她不仅长得漂亮,学习成绩还特别好,老师们也非常喜欢她,作为镇中学的校花,一到放学的时候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群熊孩子献殷勤。她考上县高中的时候,村里人说这山沟里要飞出金凤凰了,这更让她爹冯雪庆高兴的合不拢嘴,每当和别人聊起这个闺女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
可出人意外的事,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大家都看好的丫头突然就辍学在家了,冯家人对于村里人的询问不愿多说,后来为了消除大家的疑惑冯雪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读再多的书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对于这么一块读书的料不让读书,大家都埋怨着冯家的不是。
二婶在家里一晃就到了18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时有人向冯雪庆提亲,冯家就把她嫁给了邻村路家庄一个家境殷实的人家,谁曾想不到一年路家突然退婚,一时轩然大波,风言风语在村里满天飞。
从这些流言蜚语的传言里得知,二婶在上县高中的时候,由于样貌出众学习优异,县里一位有势力背景的公子哥纠缠着要和她处对象,这位公子哥依仗父辈的淫威网络了一批狐朋狗友搞了一个‘斧头帮’,在学校飞扬跋扈狐假虎威搞得天怒人怨,老师和同学迫于他父亲的势力背景敢怒不敢言。
那时的二婶心高气傲是不会把这些浪荡公子放在眼里的,高衙内似的公子哥看死缠烂打追求不成就色胆包天的强暴了她,二婶这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就此凋谢了。
出了这样的丑事,二婶自然没办法在学校呆下去,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冯雪庆前去讨要说法被对方一通威胁后感觉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了闺女的名声只能打落门牙往肚吞,在对方赔了一笔钱后最终息事宁人。
虽说冯家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各种恶毒的传言中,二婶婆家终于听到风声得知内情,就这样二婶被婆家无情的扫地出门,再次跌入无底深渊,她除了哀叹上天的不公,已是无路可逃。
雪上加霜的是农村好事者多,碎嘴长舌妇更是恶毒,各种版本的传言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在她撕裂的伤口搅扯,让她一度神经错乱,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四肢麻木,大脑麻木,神经麻木,麻木的感觉不到悲痛,宛如行尸走肉,只能听天由命。
农村人尽管物质贫穷可都讲究个脸面,谁也不敢把这个被婆家踢出门的‘二手货’娶进门,何况又是那样一个女人,还不得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
有这样不堪经历的女人注定一辈抬不起头,冯雪庆看闺女整天窝在家里遭人指点非议,难免哭丧个脸长吁短叹,见人矮三分,再也没有以前和别人说起闺女的骄傲了,现在倒变成了他的负担。
二婶娘看闺女在背后偷偷流泪终是心疼,她知道孩子的委屈,可她天性胆小没有主见,遇到这天大的事更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只是心疼说着隔靴挠痒的安慰话,然后娘俩抱在一起哭得如同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