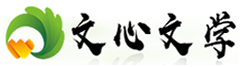老屋门前那条路[ ]
老屋门前有条小路,小得像一条蚯蚓,一条刚从地里蹿出来,活蹦乱跳,纤细而散发着土壤亮色的那种蚯蚓。它弯弯曲曲,田埂一样的质地,它是祖祖辈辈的脚印汇成的一条小路。
小路的西边,一排高大的喜树,挺直着腰身,为小路站岗,间或夹杂几棵果树,结满了红的绿的圆果子;小路两旁绿草如茵,草丛中散落着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招引蝴蝶在野花上翩翩起舞。
小路的东边有棵高大的酸枣树,一到夏季,哪怕是最热的天气,酸枣树上都会有许多长“鸣”不断的蝉儿,十几只甚至更多的蝉儿同步鸣叫,有时,我们会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靠上前去,往往我们还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来,“扑啦啦”一阵响,一群蝉儿向远方飞去,留给我们的是蝉儿排泄的废物,淋到我们的头上、脸上,合上满身的汗水,让人凉飕飕的,我们起先是猛然一惊,转而互相嘲笑,甚至埋怨,为什么我们没有捕到蝉儿呢?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酸枣树就像一把巨伞,为我的童年遮风挡雨,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树上那诱人的果实。站在树下就能看到树上密密麻麻的酸枣,一个个黄灿灿亮晶晶的,这些李子般大小的酸枣,或高或低的垂挂在树枝上,把酸枣树装扮得艳丽多姿!我经常仰着脖子,两眼睁得大大地,看得口水直流。特别是中午,饥肠辘辘的我那把热情之火,在瞬间就熊熊燃烧起来,让我哧溜哧溜几下就爬了上去,肚皮让树皮搓得通红,甚至疼得呲牙咧嘴也不在意,坐在树杈上摘酸枣吃。几年下来,炼就了我高超的上树本领,让我偏向于树栖动物。
清晨,太阳像一个圆圆的大红灯笼悬挂在硕大的蓝色门框上,是那么的醒目,又是那么的别致。站在小路上,头顶的酸枣树、脚下的小花小草在朝阳的抚摸下,充满活力,微笑的脸上似乎还残留着调皮的泪珠。
傍晚,红日西沉,暑热稍褪,晚出的月亮爬上屋脊,我们就会习惯性地将洗好的竹床竹椅之类的纳凉器具搬出来,放在小路上,放在酸枣树下。在繁星满天的夜色中,人们在凉席上或坐或躺,随意地摇着芭蕉扇,驱赶边飞边嗡嗡叫着来凑热闹的蚊子,聊着轻松的话题,国家大事、村里新闻、还有各种马路消息,萤火虫在空中游弋,时明时暗。二哥高兴起来会哼上几句怀旧的歌谣,五哥也许会来几句“蔡鸣凤在大街思前想后,想起来家园事珠泪交流,悔不该在家中口角争斗……”之类的花鼓戏。母亲则摇着芭蕉扇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在那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酸枣树和着那动听的故事不知陪伴我度过多少美好的夜晚,让我在“月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慢慢地成长。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还是下雨天,僵硬的泥土一下子变得松软,小伙伴们披上塑料布,赤着脚从家里冲出来,汇聚到这条小路,有拿木棍的、有拿水瓢的、有拿铁锹的……在雨中,我们跑啊、追啊、笑啊。大人们坐在屋檐下,聊着自家的或别家的闲话,探讨今年的收成,偶尔有个婶婶放下手中的针线,向雨中早已变成“三花脸”的孩子大吼:“你个臭崽子,刚给你换过衣服哪!”我们在原地稍停片刻后,随即又在雨中荡漾开了。
下雨天,时常有路过小路的人跑到我家来躲雨,这时,母亲会急忙招呼客人坐下,递上毛巾,端上茶水,父亲也会舒张开眉头,简陋而有些暗黑的茅屋,顿时有了生气。看着这些人和我母亲父亲打招呼,然后说笑、聊天。听他们讲这讲那,我似懂非懂。有他们在,母亲和父亲的话也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我希望他们就一直这样待在我家,一直和我母亲父亲在一起聊,我希望屋外的雨一直下,下的更大一些。
渐渐的,我发现父亲居然和我一样,也喜欢看小路上的“风景”。有时他倚在门边,有时和我坐在一起。他抽着旱烟,身子动也不动。从烟的缭绕中,我看见父亲的眼睛总是向前眯起,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又好像在想什么事情。他曾指着小路对我说:“这条路是通广州的。”在我的脚步还没有迈出一座村庄的年月,父亲的话像是门缝里投进来的一线阳光,让我知道,门外还有一个世界,更宽广博大,更玄妙神奇。从此,我开始专注地凝望这条小路,我想,有一天,我一定要沿着这条小路,阅过路边层层叠叠的风景,去县城,上长沙,到达广州。
后来,我上学了。每天,我走出家门,先沿着这条小路,再走上防洪堤,去堤上的小学读书。我开始有了老师,有了同学,有了课本,我从课本里慢慢地打开了外面的世界。
再后来,我考取了县城里的高中。那年高考后,我真的远远地离开了我的村庄,去长沙读大学。然后是在广州工作,像春燕衔泥般地的筑巢垒窝。我知道,我顺着那条小路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已经离开我的村庄很远很远了。
渐渐的,我读懂了父子情,读懂了母子泪,读懂了门前那条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