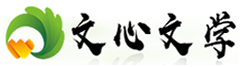温暖的柴火[ ]
六七十年代,乡村家家户户以烧柴为主,需求量大,柴火短缺是常事。
每年秋天,我都会去漫地里捡柴火。这柴火,其实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已行走到生命极限的树枝,或是生长在田间地头的零星灌木。
放学回家,拿起竹筐,架一个竹耙,搭上肩就走,哗啦哗啦满野瞎转悠。在本来就光秃秃的地里硬是搂出一把把柴火来。风起时,眼看一根树枝就要被吹向远方,还会紧跑几步,把它抓回来,让它回到自己掌控的柴火队伍里。
累了,舒展在草地上,望着高高在上的丛林,期待更多的树枝死去。急了便爬上树,把那些要落不落的枝条折下来,悄悄压在筐底。
当夕阳快要吻到西边的屋顶,我就背着满满一筐柴火往家走。遇到邻家婶婶嫂嫂,她们或许会夸赞一句:“九满,真勤快!”此刻,带着收获的成果,喜悦早已占据了整个内心,对于这种鼓励,还是毫不推辞地欣然接受。
柴火灶可不是吃素的,我捡的这点柴火远不够它享用。弄柴火还得靠几位兄长。
秋收后,兄长们沿着蜿蜒曲折的田埂,把队里分配给自家的稻草、棉花秆依次收回家。于是,房前屋后便冒出一个个蘑菇状的柴垛。
稻草收回家后,父亲总要找几个晴朗的日子,在屋面上发黑的茅草中补充新生的稻草,用新生的稻草整修过的房子就很难漏雨了。
做饭的时候,母亲蹲在灶膛口,棉花秆放进去,再抓一把稻草引火。擦亮火柴,放在稻草下,火苗呼地一下蹿起来,伴着棉花秆的噼啪声,火势很快就旺了,随后,大自然的美味也弥漫开来。灶膛前闪烁着的火苗,舔着锅底,也映着母亲慈祥的脸庞。当然,如果风向不合适,烟就会逗留在屋子里,让人体验“烟熏火燎”的内涵。这时,母亲会打开门窗,让弥漫在屋子里的烟飘出去,飘向更远的地方,烟太大太浓时,母亲还会拿着芭蕉扇,使劲地摇着,好让烟快点儿散开,仿佛在说:“出去走走,好男儿志在四方!”
过年过节或来客人时,需要启用大锅,稻草、棉花秆过火快,眨眼就熄了,不经烧,只得退居二线。经烧还得老枝、树干等硬柴,它们是烧火材料的不二之选。父亲平时不怎么在灶前灶后帮忙,这时候,父亲会和母亲一道烧菜做饭,父亲坐在灶口前往灶膛子里添柴,母亲系着围裙站在灶前炒菜,母亲会不时提醒父亲,烧大火,父亲嗯一声,加点柴火,有时母亲说让火小一点,父亲也是嗯一声,就用火灰埋一下大火,父亲话不多,但很耐心地听着母亲的唠叨,两人相互配合着。看到父母协同做饭,我感到心里有一种幸福和安宁。忙碌中,母亲会把平时积攒的、舍不得吃的食物都拿出来,也会在铁锅里大显身手做足文章,蒸腾出大家喜欢吃的饭菜。各种颜色你来我往,各种瓶瓶罐罐接踵摩肩。屋子里,香味飘飞。红通通的灶火,噼噼啪啪的声响,喜人的颜色,富有人情味的烟火,让人仿佛置身在一个充满喜悦与和谐的美好世界里,一个幸福可以绵延到地老天荒的童话里。
凛冽的寒冬,室外寒风呼啸。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听炉火“轰轰”地烧着,看茶壶“扑扑”地吐着热汽,闻烤红薯“呲呲”地喷香。母亲那些有趣的励志的民间故事也是在这时候讲给我们听的,她讲《白蛇传》,讲白娘子,讲水漫金山寺,讲大战法海。说得我幼嫩的心早早立了志向,长大要做白素贞一样,要那么波澜壮阔地爱和恨。她又讲到陈世美和秦香莲,母亲说起秦香莲,一边说一边叹,让我想起那天背着孩子到我家门口要饭的那个外地女子,会不会又是一个“秦香莲”……一家人,说着笑着,特别温馨美好,特别富有诗意。
那时候,常听人说:“仓里有粮,心中不慌”,其实,家有柴火,农家心里才会踏实。冬天,母亲从柴垛中取几捆上好的稻草铺在床板上,睡在稻草制作的“席梦思”上,寒夜里,家人就不至于太冰冷;当母亲从柴垛上拽下一把干燥的稻草,细心地铺进鸡窝,从此,这里每天就会有几枚令人嘴馋的鸡蛋;当父亲给猪窝铺上厚厚的稻草,猪们在寒冷的日子里,就能暖暖而美美地做着它们的黄梁美梦……
一晃一年过去了,一晃多年过去了,我就在柴火的温暖下度过我的童年时光。以至于到现在,不管在哪,只要遇到我“熟悉”的柴火,我就会想起童年、老屋,年纪尚轻的父母,一起捡过柴火的童年伙伴,让我情不自禁地对眼前的这些柴火投去亲切的目光,就像在异乡遇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