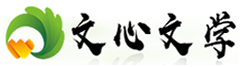甲子回眸:我在中国和美国的求学与工作之路[ ]
2025年是我的甲子之年。 六十年前,我出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六十年后我是美国大学的英语教授,工作、生活在世界上最发达、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 有诸多的感慨和思索。 这六十年来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求学和工作之路呢?有步行七年经历过饥饿、贫乏的中学之路,有火车载我告别村庄从而改变了我一生的七年的大学/研究生之路, 有传道授业、为人师表的七年的留校教书之路,有发奋攻读、获取美国文学博士的留学之路,有敬业爱岗,将爱心、耐心和知识贡献给美国下一代的二十多年的教育之路,还有夹杂在来美二十八年中的移民之路,和认识世界,拓宽见识的国内/国际旅行之路。每段路程各不相同,连接起来铺就了我的人生之路,有曲折,有挑战,更有希望,有收获,有满足。 从头叙起,相信能给读到本文的读者以激励和启发。
中学求学之路
我七岁半被父母送到村小学读书。听讲、做算术、背课文都是我不喜欢的。 学校是由一栋破败的祠堂隔离出来的空旷的房间,没有吊顶,仰面看见大梁和木椽,夏日炎热,冬日寒冷。我衣衫破烂,书本和练习本夹在腋下因为没有书包。冬天坐在四面通风,窗纸经常被学生捅破的教室里,耳朵、手脚都冻得红肿, 根本无法安静坐下来听讲。老师的处罚又经常发生, 稍有违规即遭到老师的教鞭。
四到六年级时,我来到二里以外刚建成的小学读书。学校建在四面无人的田野里, 一排瓦房用作教室,一排窑洞作为教师办公和休息室,教室墙面和窑洞用砖砌成, 学生桌椅由土坯垒成,上面贴有一层木纹纸。教室前面的空地和操场皆为黄土,零零散散地栽种着一些杨树。
我每天步行三趟去学校。早上天刚蒙蒙亮就与同伴出门,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去学校,下午回家吃晚饭,晚饭后再去学校上晚自习,八九点左右回家休息。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学生们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条件稍好的学生下雨时可以穿一件廉价的雨衣。雨伞则极为奢侈,很少见过老师和学生用过。没有条件的学生就将装过化肥的废塑料袋折叠披在身上挡雨。雪特别厚的时候,学生们拿着一把木锨推出一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其它同学尾随其后,如行进中的小分队。
这样的路走了三年,没有觉得有什么负担。天气转暖,草木发芽时,一群十二三岁的青少年相伴而行竟有无穷的乐趣。我们互相追逐,打闹,摔跤。当时还流行用费书折成的纸炮,放在地上,看谁能将对方的掀翻就告赢。我们忘情地玩耍,经常误了上学和回家吃饭的时间,遭到老师和家长的训斥。
家里生活一贫如洗,衣衫褴褛自不必说,步行中的风霜雨雪自不必说,单是那饥饿、贫乏和羞辱就让我常常低下了头,不敢正视老师,同学,更别说在课堂上发言。 家里吃的主食只有玉米面馒头、玉米糁、土豆和红薯。但即使这样,供应仍不充足。早上上学前肚子饿时有时连玉米馒头和红薯都没有,只有饥肠辘辘挨饿等中午回家吃妈妈煮好的玉米糁子加红薯稠饭。又由于妈妈一年四季在生产队劳动,包括数九寒天 ,无法按时给我准备好午饭和晚饭,我总是上学迟到,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前面,并书写检讨念给全班同学听。 还有交不出几元钱学费的时候。看到其它同学都按时交了学费,只剩下没交的几个同学在班上被点名,我的脸变得通红,身上冒出紧张的冷汗,恨不得地上冒出一个洞让我跳下去,心里不由得生出对父母的抱怨:为什么其它同学能按时交上学费,我们不能呢?
使我脆弱、敏感的心得到安慰的是我的成绩。虽然我不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尖子生,但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语文课还特别突出。老师有时让我站起来领着全班同学朗读,让我脸上有了一些光彩,觉得我也有比其它同学强的地方。
真正让我对学习感兴趣则是我考上初中二年级开始寄宿生活以后。1979年我还不到十四岁,背着妈妈给我做的一些烙饼和姑姑给的一床棉被,步行到五六里外的一所初级中学读书。每周往返两次从家里带干粮,中午和下午可以从学生灶买到一碗玉米糁,晚上睡在可以容纳三十多人的地铺上,身子底下是坚硬的土坯台和铺在上面的褥子。寄宿生活比家里要艰苦得多。在家里吃饭虽然只有玉米、土豆和红薯,但刚出锅的饭总是热的。全家围坐在一个矮桌周围,爸爸手里捧着一个大瓷碗,四周围绕着五个饥饿不堪的孩子,个个吃得津津有味。
这种寄宿生活,如果不是心里揣着一个目标,一个梦想,一条道路,是很难坚持两年的。好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懂得的事越来越多,越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相信只要目标明确,迎难而上,我就可以走出这条艰难的求学之路,为自己开创一条美好的未来。想到这些,脚下的道路突然变得宽敞,明亮,路两边高大茂盛的白杨树也在风中向我招手,让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策马千里的豪迈。
这种决心和动力让我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我成了班上和年级数一数二的尖子生。我在英语和语文科目上更有灿烂的表现,能将老师布置的课文倒背如流,作文被当作范文登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我在全校三百师生面前流利地背诵英语课文,让大家对我这个个头矮小,皮肤黢黑,衣着破烂的农家子弟刮目相看。 我衷心感谢我的英语老师翟建民和语文老师马俊仓。他们早期发现了我在外语和文学方面的天赋,并适时地引导和鼓励,让我在这两门课上锦上添花, 开启了我一生以外语和文学为伍的教育生涯。今天我能在美国大学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文学教授,我的起点开始于那所遥远、落后的农村中学。
初中毕业以后,我来到距家十五里外的高中读书,脚下路途漫漫,照样从家里带上干粮,一瓶咸菜,每周往返一次。春夏步行最容易,秋天阴冷的连阴雨和深冬刺骨的寒风让我欲哭无泪,欲罢不能。这时风也急,雪也大,掀起本来就不御寒的薄衣。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心里不住地诅咒这该死的天气。为什么屋漏偏遇连阴雨,这老天还有公道吗? 可是心里虽然憎恶,接下来的路还得自己走,就再咬紧牙关,继续前行,就这样我来来回回地走了两年,路程虽然艰难,但远方的目标却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拼命读书,希望通过高考改变我和家人的命运。在我就读高中的1981-- 1983年,高考这两个词对偏僻的农村学生有着神圣的诱惑。它代表着身份、充足、金钱、城市和现代。跨越了农村这道门槛,能将自己脱胎换骨,从一个农村的穷小子变成商品粮户口、领取固定收入的城里人。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怀着这样的梦想,我们对脚下遥远的、泥泞的、寒冷的道路都不十分在意。他们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临时障碍,只要能考上大学,即使再大一点的不适,再遥远的距离,我们也能克服。四十年后回忆起这段艰难岁月,仍惊叹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希望和执着。
大学/研究生之路
1983年我顺利考取西安外国语学院(2006年改为大学)英语系,告别了步行去学校的历史。九月二十日开学那一天,一夜难眠的我一大早就从土炕上爬起来,准备远出的行李。爸爸早已请木匠和油漆匠给我做了一个大木箱,里面装着被褥、衣服和书。不巧的是,连续半个多月的连阴雨使任何马车和机动车都难以在泥泞的路面通行,最后我和哥哥用一根长木棍将箱子抬起,在雨中步行了三个多小时赶到了十七里外的火车站。远远看着冒着白烟停靠在车站上的长长的绿皮火车,我的心咚咚直跳,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忘却了一路上的泥泞和负重,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跨到窗明几净的火车前。
我跳上了火车。第一次置身于这样敞亮、干净的车厢,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昨天我还冒着小雨和家人在泥泞的田里平整土地等待给小麦下种;今天我换上了一身新装,坐着这列宽敞、明亮的火车去省城读大学。火车上一排排干净整洁的座椅、两个座椅间安放妥帖的小桌、行李架上摆放有序的大包小包告诉我即将告别一种旧生活而开启一种全新的生活,且随着旅行工具的改变,我的人生旅程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之一就是脚下的道路,再没有了泥泞的道路和泥土的校园。学院到处是水泥马路,即使在水泥不易到的羊肠小道,也用砖铺设。学院占地两百多亩,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大礼堂、餐厅、校医院、学生和教工宿舍、家属区掩映在巨大的梧桐树中。能在这样的环境学习和生活真是莫大的荣幸。1983年的大学入学率是23%,是由录取的人数和预选后参加高考的人数得出的。如果将所有高中毕业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将是个位数,所以当时能考上大学被视为天子骄子。我也是一百多人的村庄考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尽快安顿下激动、骄傲的心情投入到学习中。我的大学梦想实现了,但真正的大学生活才刚开始,我期待着它能将我塑造成一个有抱负、有知识、有修养、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八十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国家急于改革陈旧的规章制度, 吸纳从西方传来的知识和经验。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主要外语语种齐全的高校,学院首当其冲地做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那时学习外语非常时髦,毕业生去向大多是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经常到学院访问和讲学的外国友人也很多,学院也常年聘请了十几位外国专家和教师,加上刚从国外拿到学位或进修回来的教师,我在大三大四的教师阵容相当强大。我得益于当时在西外交换的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莱斯特·巴勃(Lester Barber)教授、杨百翰大学芭芭拉·杰克布斯(Babara Jacobs)女士和刚从澳大利亚和美国拿到硕士学位的杜瑞清和惠宇副教授,和像周龙如和李嘉祜那样全国知名的大牌教授,从他们那里,我掌握了英语语音、语法、翻译、文学、文化等知识,为我以后毕生从事英语文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随着知识的增长和阅历的扩大,我也更多地了解了自己,在学业和做人方面变得更加自信。
课堂以外,我也努力拓宽我的视野。周末我一般去其它大学拜访中学时代的同学,参观他们的校园,交流读书和生活心得。有时也去西安和周边的文物景点和商业中心游览,感受改革开放给西安带来的变化。一九八七年考取研究生后,又得益于研究生访学的机会参观了北京、上海、济南和杭州。除了感受首都的宏伟、上海的摩登外,我有机会拜访了对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 有研究的几所大学的著名教授。 这次访问无论对我的视野和学术追求都大有裨益。也是在这次访学中我得以认识我未来的夫人,她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攻读英语硕士学位。她的知性、善良、包容是我一生的祝福。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荣幸地被英语系留下来任教,一开始就担任四年级口译课教学,反映了英语系主任何其莘教授和其它教授对我专业能力的信任。后来,我又担任四年级的美国文学选修课教学。我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在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成绩,成为一名深受同事和和学生尊重的青年教师。
做教师也是我的梦想。高中时期我就十分羡慕能将知识难点清楚地讲给学生的英语老师赵根荣。他对英语语法了如指掌,寥寥数语就将一个很复杂的语言现象如虚拟语气、被动句讲得水落石出。大学时代我更倾慕于周龙如、杜瑞清、惠宇等教授。他们勤奋努力,知识渊博,为人低调,爱岗敬业,在为文和做人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学读博之路
1997年8月15日,我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出发,短停上海,转机旧金山、匹兹堡到达我要读研的鲍林格林州立大学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附近的特利多机场。这是我有生第二次坐飞机,脚下是万米高空下的山川和原野。从美国山脉纵横的西部向东延伸,一直到良田万顷、一眼望不到边的中西部平原。机场离鲍林格林小镇二十五英里。接我们的车子在宽敞平坦的州内公路上行驶,两边的黑土地上生长着绿油油的、茂盛的玉米和黄豆,和家乡黄土高原干旱、贫瘠的土地不可同日而语。
鲍大是一所占据3000多亩土地的州立大学,既无大门,又无围墙,大学的通道和镇上的道路、街区相通,汽车和行人可以自由直入。东部是高尔夫球场、停车场、足球场、网球场、冰球场和能容纳万人的橄榄球场。校园中部和西部是学生宿舍区、体育馆区和教学区 。体育馆是一座位于地下三层的巨型活动中心,有田径馆、篮球馆、墙球馆、健身馆、体操馆、游泳馆等。仅游泳馆就有两个,附加以热水浴缸和桑拿室,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教学楼皆四五层左右,分散在校园中心,每个楼之间都有大片的绿地和树木 。每个教室窗明几净,铺着整洁干净的地毯,配有现代化教学仪器如电视、投影仪和电脑等。
同它一流的设施一样,鲍大的师资也非常强大,他们皆毕业于美国的名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执安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能在这样的名师指导下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让我终生受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