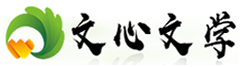从前的冬天[ ]
从前的冬天,村庄的田间地头一派空旷。
天空湛蓝,云朵在天上流动,不断地变幻着模样。阳光洒在收割过后的原野上,大地像刚生过孩子的母亲,幸福地舒展在开阔的晴空下,躺着。哪里是水田,哪里是旱地,哪里是田埂,哪里是沟渠,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些空地里,长了些杂草,牛儿在里面埋头享受嫩草的美味,时不时甩一下尾巴,显出一种难得的轻松;三三两两的麻雀放低翅膀,在杂草间寻觅庄稼人遗落在地上的稻谷……
忙活了大半年的庄稼人,日子也慢了下来。午后,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斑驳的光影。草垛边、墙根下、篱笆旁坐满了晒太阳的老人,有的抽着烟,有的听着收音机,有的闭目养神,悠闲自得地享受这冬日的暖阳。我也时常偎在母亲身边晒太阳,一边看她做针线活,一边玩耍。太阳照在我和母亲身上,照在她黑黑的头发上。母亲一边忙碌着,一边跟我聊她的往事。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母亲像这冬日里的阳光,让我感到温暖、幸福。
冬天,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抓鱼了。我和小伙伴们,在小沟里,先用泥土一段段地把小沟截断,然后用陶瓷盆、木桶从内将水一盆盆一桶桶地舀到外面。当小沟里的水只剩下中央一点点时,那些鱼啊泥鳅啊便在水里乱蹦狂跳,做最后的挣扎。我们开始捉鱼,摸着捞着。回到家后,把鱼虾放在清水中养上小半天,然后除去内脏,清洗,加上豆豉、辣椒等配料水煮。随后,我们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道荤菜。
我特别喜欢下大雪的夜晚,村庄很安静,静得没有一丝声响,连日常狗吠、人喧闹的场景都似被雪冻结了。常年睡灶头的小花猫嫌冷,就一个鱼跃跳上床来,眼尖手快的五哥,一把搂过小花猫,放到自己的被窝里,和小花猫抱团取暖。偶尔传来一声枯枝断落或狗撕咬的声音,让早早钻进被窝的人们在这些声音里醒来又睡去,只觉得夜好长,日子好长。
清晨起床,推开门,刺骨的寒风挟裹着鹅毛大雪,呼啦啦地在混沌而迷离的空中旋转,一会儿上卷,一会儿下沉。茅房上,柴垛上,树枝上都蒙着毛绒绒的雪,目之所及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往日的枯草绿麦已不见了踪影,天和地的界线,似乎也不那么清晰了。
收拢翅膀的鸡群紧紧相依着蜷缩在背风的角落里不动声色,好像只要扇动一下翅膀或是挪动一下脚步,刺骨的冷风就会从移动的缝隙里钻进来。平日里与鸡你追我赶的小黄狗也将身体蜷曲成一团贴着鸡偎在那里,它们前嫌尽释,在凛冽的严冬里摄取彼此的体温御寒。
我和五哥炒点剩饭吃后,全然不顾外面的严寒,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一头扎进银装素裹的世界,踏着积雪去离家半里地的村小上学。农田里、鱼塘中、沟渠下都结上了一层薄冰,连晒谷场上的小水洼都冻成一块冰。路上的行人潜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头顶着刺骨的寒风匆匆前行。树上的喜鹊一点也不怕冷,在光秃秃的树杈上飞来跳去,“喳喳喳”地叫个没完,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好心情。麻雀在电线上“叽叽喳喳”,像在商量着去哪里觅食。
晚上放学回来,一进屋,灶间的柴草燃烧的温度和大锅里冒出的蒸汽,立刻把冻得直禁禁的我从上到下包裹起来,书包顾不得放下,先把冻得红肿的小手伸到灶膛口,上下左右反复翻转。
从前的冬天是那么的寒冷,冷得人们不想出门。这时,最温暖的莫过于屋子里燃烧着的火炉。我把脚摆放在火罩上,炉里的火暖烘烘地烤着,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二姐纳鞋垫,三姐织毛衣,母亲坐在临近窗口较亮的地方纳鞋底。父亲嘴里叼着一杆吞云吐雾的烟锅,和我们谈论着“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瑞雪兆丰年”等古老话题,父亲的土话里,句句都是家常饭菜一般的道理。任屋外凛冽的寒风呼啸,屋内一片祥和、温暖。偶尔,我会跑到谷仓里摸出几粒稻谷,撒到火炉边,心里也就有了盼头,不一会,噼噼啪啪,屋子里弥着爆米花的清香,那是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啊!
在那万物规避寒冷的时节,似乎只有屋顶烟囱上冒出的缕缕炊烟,才能彰显出村子的生机与活力。黄昏,屋外扬风搅雪,早早就黑了天,母亲点着煤油灯,在灶屋里奏响起锅碗瓢盆的交响曲,笨实的铁锅里,发出沉闷而愉快的声响,木柴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爆裂。不一会,就有香气飘出来,让人垂涎欲滴。开饭了,父亲把矮矮的饭桌放在堂屋中间,我赶紧把各式各样的小板凳、椅子围着饭桌摆上一圈,母亲从锅里往外收拾饭,二姐把炒好的菜放到桌上。全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开始了一天中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从前的冬天,不只有彻骨的寒冷,还有清晨的炉火、午后的暖阳、黄昏的炊烟、熟悉的饭菜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