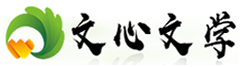故乡,拴着我的心[ ]
小时候,我的故乡很不起眼,一直以来就靠村后那条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防洪堤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艰难的联系。我很无奈出生在这里,很多时候,我非常憎恨它,憎恨它的落后,憎恨它的贫穷,憎恨它的偏僻。而且,当时的我,固执地以为自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里。
那时候,乡亲们的日子过得都很苦,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改变什么,他们似乎习惯了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每天天还没亮就起身,匍匐在田间地头,全身晒得黑不溜秋,天黑透了才会回家。夏季的阳光十分毒烈,父辈们俯身在水田里,用长着水泡的手,一兜兜地收割早稻,又一兜兜地把晚稻插下去。我看到他们额头上的汗水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我看到他们湿透的衣裤上,成片成片的汗碱霜花般结晶成盐。猪和牛在河滩上散漫,驱赶它们的老人或小孩一步一趔趄。
偶尔,我也不得不俯下身体,双脚深陷在黑臭的水田之中,用镰刀、锹和锄头,一下一下,干着父辈们日日重复的枯燥的农活。农历七月天,在地里除草,稻叶像一把把锋锐的利剑,人在田间穿行,要穿长裤长衣,天上的毒日曝晒下来,一身的汗水把衣裤都浸湿透了。“双抢”时节,我抓住秧苗的根部,食指掐进泥里,一捞,一抖,秧苗完好无损地起身。秧苗的根部,稻种尖锐的壳将我的右食指刺出无数细密的黑洞。污泥沾满我的指缝,田水泡皱泡白手脚的肌肤。我的右手掌磨起无数水泡,透亮,似玉米粒大小。我曾在酷暑的田间饿得前胸贴后背还得挑回一百多斤为牛准备的粮草,我曾在酷热的中午顶着似火骄阳割完最后一兜水稻,我曾在蚊虫乱舞的夜晚弯腰弓背非要插完那丘水田。
劳累不说,饭还吃不饱。每次吃饭,母亲总是默默地先尽我们享用,剩下的她随便吃一点。青黄不接时,晚餐就是喝点粥,不够分配,母亲自己就是喝点锅巴糊。我常听母亲说:“要是天天有饭吃,就是没有菜,我也能吃两碗。”父亲更是习惯性地把我们撒落在桌上的饭粒放进嘴里,一粒,两粒……那一瞬间,我目瞪口呆!望着父亲贪婪的吃相,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我不知道这种貌似和谐安宁的状况何时可以改变,可是,我受不了这种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劳作,受不了这种年复一年的忍饥挨饿,我更受不了这种“一年盼着一年好,年年都是这件破棉袄”的穷日子。对此,我无法按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对乡村生活说出“世外桃源”“人杰地灵”“人欢马叫”等等冠冕堂皇的词汇。在我的心里,乡村的一切都充满了烦恼和焦虑,因此,逃离的想法一天比一天高涨,我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我也不止一次地发誓过: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一定要换一种活法!
自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那天起,我就发奋努力地读书,希望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年七月,我如愿地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汽车终于启动缓缓前进时,坐在车里的我毫不掩饰地长长舒了一口气,嘴角还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得意,仿佛这块土地对我多年的束缚,很快就会松开或者断裂。心中充满喜悦,俨然成功实现了人生的提档升级。因此,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走进了只长楼房不长庄稼的城市,吃上了“国家粮”,成了城市的新移民。
因为所遭受的种种屈辱,那时候,我对故乡没有切肤之爱。但是,当我远走他乡、独自闯荡时,我才在内心深处感到故乡在我的生命里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在他乡的天空飞累了,飞倦了,我期盼飞回来靠一靠、歇一歇,而故乡总是以最浓烈的情怀欢迎我、接纳我。当我在故乡的土地上汲取了足够的营养和力气时,我又可以像候鸟一样飞走。
前几天,我又回了一趟故乡。走下汽车,中年的我如蜗牛一样驼着生活和家庭的重壳,坚实得如一头暮归的黑水牛站在村囗。这时候,迎接我的是四月金灿灿的油菜花,还有扑鼻的花香和嗡嗡勤劳的蜜蜂……
走过故乡的田间地头,故乡的风越过大河的防洪堤,轻拂在我身上,暖意顿生。脚下的泥土软绵绵的,仿佛能吸走我身上所有的疲惫。村中央的那条抗旱沟边,我的思绪竟随着潺潺水流飘向远方,飘去天际,而那些牵心扯肺的思念,梦绕魂萦的怀恋,深入骨髓的凝想,逐渐酿成我美感涌流的乡情。
我发现,回到故乡,我就像是回到水里的鱼。我在这里大口大口地呼吸,看书,码字,散步。我的整个身体都被浓浓的乡情包围,我的心也有些抖颤了。“啊!亲爱的故乡!”我无数次失声地喊出声来。
我不知道在我的生命过程中,还能再回来几次,但我知道我的灵魂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故乡。故土是老态的,也是传统的,这种老态和传统让我常常无端的心生悲凉,但是,在我的潜在意识里还是眷念的多一些,那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乡情永远挥之不去,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我走得越远,年龄越大,它就扯得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