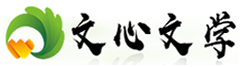人世间再也找不到我的母亲了[ ]
我的母亲,一个将我从乡村送进城市的老人,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清晨,终于承受不了岁月的摧残,走完了她九十四年的人生旅程。
从此,屋子里沸腾起来,忙碌起来,喧闹起来。
那些日子,我扬起硕大的脑袋,努力用不太灵敏的耳朵捕捉人们的议论。人们咀嚼母亲生性良善,见着谁都客气,和煦、春风满面的样子;咀嚼母亲将锅里的最后一碗饭送给生病的邻居吴大妈,让自己饿了一个晚上的故事;咀嚼母亲找她的童年伙伴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的趣事……母亲一生留下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已的事来。这些天,那些受过母亲恩惠的亲友、乡邻含泪跪拜,惦念旧情。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老人,用一生积攒的好人缘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时候,村庄很贫穷,我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苦。母亲舍不得添置新衣裳,一件外套能穿七八年。她舍不得吃好的,一碟辣椒萝卜、一碗稀粥就是一顿饭。可是,只要发现我们爱吃啥,她就尽力给我们做啥。她总是出现在该出现的时候,比如我们大汗淋漓,她会给我们递上一条毛巾,说擦擦汗,别着凉了;我们光着膀子抱柴火,她会递给我们一件长袖衣服说小心扎伤皮肤;我们口渴要喝河水,她会端着一大碗温热的茶叮嘱我们还是茶水解渴……
我的身体差,不是这个感冒就是那个发烧。五岁的时候,我出麻子,病情很重,我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阎王爷的家门口,催命的小鬼,正抖着哗啦啦响的铁链子,锁住了我的脖子……半夜,我醒了过来,一睁眼便看到了满天的星辰,在横越天际的璀璨银河岸边,1968年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向人们预示着灾难深沉的年代。
母亲仿佛把故乡田间地头的草药都采齐了,放在一个瓦缸里煎熬着。随后,母亲端着药汁,用毛巾蘸着,擦洗我的身体。我感到有些难为情,母亲说:“崽啊,你活到一百岁,在妈的眼里也是个孩子……”母亲把我的全身擦了一遍,甚至连我脚丫缝里的积垢都擦净了,我感到身体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这样干净过。渐渐的,我汗流如注。我惊喜地感到身体有了知觉。我沉静地进入梦乡,第一次没被噩梦惊醒,一觉睡到天亮。待我病愈,母亲瘦了一圈,眼窝凹陷,脸色蜡黄。
上学的日子,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回来,先叫我洗手,然后从锅里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围在一起用餐,唠着家常,共享家庭最温馨、最美好的时光,感受那贫瘠岁月里滋生的温馨恬淡。母亲从不允许我们浪费粮食,总是要我们吃尽碗里最后一粒饭。在我们迷恋一些玩具虫鸟的时候,斥责我们玩物丧志,教我们一些生僻难懂的话,比如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常怀感恩之心,常为感恩之行。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等等。这样的母亲,像是教室里的那块旧黑板,方正、黑白、传统。
母亲是坚毅的,她办事的干练甚至超过了父亲,少了一些瞻前顾后的忧虑,表现出认定一条路只顾往前走而不左顾右盼的专注和果断。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县城上学,因为离家远,吃住都在学校,生活费用一下子涨了许多。母亲决定由她的那几个分了家的孩子们一起来承担我的学费,大哥知道后,便引经据典地规劝母亲让我辍学回家务农,二嫂更是跑到我们家里来,叉着腰在母亲面前大放阙词。他们对我更是一脸的厌烦,目光冷酷,好像对我充满了仇恨。面对儿子儿媳们的消极态度,母亲是痛苦的,更是焦灼的。我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母亲那沉重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几经权衡,母亲终于对她的孩子们发话了:“九满能上学,绝对不能让他回来耕田,大家一起想办法,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供他上学!”多好的母亲啊,如果没有她的坚持,哪有我的今天!
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工作。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幸福地围着灶台,用她那灵巧的双手,奏响锅碗瓢盆,吟唱油盐柴米,将普通平常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植入她的情怀,调进故乡的色彩,融入我童年时的味道,把我在家的日子,演绎得充满诗情画意。因为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工作,所以母亲很是稀罕我在家的日子。不管做啥事都“九满!九满!”地喊,从她欢快的喊声中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兴奋和满足,我知道那不是要喊我做什么事,而是希望我能多陪陪她……
如今,我的母亲没了,人世间再也找不到我的母亲了,而母亲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母亲那千言万语的叮嘱,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也相信,我的母亲,她不会走远,她是那么地爱我,她一定会换作另一种方式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照着我……此刻,她的灵魂一定正在佛尘之上,俯视着她一辈子操碎了心的我,她一定不舍得走,她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