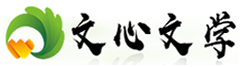仓促地到了老年[ ]
不知是哪一天,也不知是哪一年,白发悄悄来了。刚开始,发现一根,就拨掉一根,发现两根,就无奈地拨去一双。后来,白发越积越多,多得拨不过来了,我才说——随它去吧!
整个人也像午后五六点钟的太阳,虽然温暖依旧,却有些力不从心。
生活上,喜欢安静了,不怎么爱热闹了,越来越喜欢怀旧了。
对一些事情也不会较真了,特别是自己亲近的人,能包容就包容了。
渐渐地理解和贴近妻子了,听得进她的唠叨了,愿意陪她散步了,也知道拉她去买这买那了,我甚至替代她承担了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我也会带女儿去看荷花了,发了工资不再直奔银行柜台,而是给女儿买一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在她最想圆某个梦而我又有能力的时候帮她圆了……
个性平和了许多,对别人的眼光虽然偶尔也会在意,但更多的是学会了放下,已全然没有了过去的霸气。也能和自己的工作和平相处了,不像以前那样勤奋地向“领导”的位子攀爬。
烦恼的时候不再发牢骚,静静地看着、听着、想着。心里有再多的委屈,都不会随便倾诉。身上有再深的伤痕,都不会轻易表露。尽管活得很累很苦,甚至身心疲惫,依然面带微笑,依然面不改色。
没那么愤青了,遇到不公的时候,会告诉自己,社会就是这样,似乎已看破红尘。遇见弱者还是会心疼,还是会帮助而不会再抱怨。
似乎什么都看得很淡,似乎什么都看得很清,不再去计较那些种种。偶尔吃了亏,也懒得去找人拚命。曾经为了金钱、地位、荣誉甘愿牺牲身体,现在为了生命可以抛下一切。
渐渐地讨厌酒局、KTV,喜欢亲近自然,喜欢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闲暇时间主要用来买菜、做饭、上网、读书。偶尔写作,埋头于一些虚拟的故事当中,将自己经历、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垒成文字,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思维里码砌出自己想要的精彩。在文字中,快乐着自己的快乐,幸福着自己的幸福,悲伤着自己的悲伤。
前几天,侄女小玲从花都过来广州为我庆贺五十岁的生日,带着她的女儿到我家里。一见到我,小玲便对她的孩子哄着笑着说:“叫外公!”
外公!那个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满崽,已经做了“外公”;那个爱偷着溜下湖去采莲的顽童,已经成为一个脸上挂着固定笑容模式的老男人;那个背着小书包,里面还偷藏着几个番薯蹦着跳着去上学的少年,已经年届五十……
回望自已走过的足迹,犹如穿过一条悠长的时空隧道,心灵一次又一次震颤。年少时忙求学,忙进城。“进城”,这个如今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滑稽的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却如日中天,铁骨铮铮,代表着挑战与敢打敢拼,代表着优秀与成功。那时,有千百万像我这样的农村学子通过上大学离开故土,向陌生的城市涌来,像一大波一大波被月球和太阳引力诱惑的潮水。
城市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打掉牙齿和血吞的坚忍,以及对人性良善死不悔改的迷信。为了所谓的前程,我舍了命地去打拼,几乎把自己活成上紧了发条的钟表,整天处于焦虑惶恐之中,担心这没做好,担心那没考虑周全,担心这样会被责怪,担心那样人家会不高兴……
不知不觉中,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那些曾经以为会一辈子陪在身边的亲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发现他不见了;那些来来往往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悄悄成为我生命中的过客;许多教我做人道理的老领导已经永远离开,只留下日渐模糊的影像;许多过去的同事、朋友已经失去了联络,散落在未知的东南西北……
翻看从前的照片,幅边已经泛黄,在阳江闸坡十里银滩的两个人,笑容熟悉而陌生。那时候,我还在开阳项目工作,利用国庆假期携妻带女去闸坡旅游。我坐在沙滩上,侧身看妻,妻看过来的眼光真挚而美好,笑容亦是灿烂的。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于今的“闸坡”已被“海陵岛”替代,而我,已在号称“东方夏威夷”的海陵岛混沌数年。
前些日子,同事小张眉飞色舞地对我说:“九满,昨天我们去海陵湾拾海螺摸蛤蜊了,拾了摸了还不算,拿回食堂洗净烤来吃,买了啤酒,喝着闹着不醉不收兵。”多年轻的人,多年轻的事。“去吗?九满,我们今天还去。”小张怂恿我。也许是害怕,也许是不害怕,也许是担忧,也许是不担忧。苦笑,摇头,我哪里敢去,我已经老了!若是随他们而去,遇到涨潮怎么办?巨浪涌过来,我哪里还跑得动!
一切来得这么悄然,一切来得这么无情,让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吞噬着自己,让我感悟生命的宝贵,让我越来越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越来越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已经来临的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