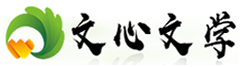故乡的土地[ ]
自从40年前离开村庄到县城上高中,我就觉得自己与家乡故土的情感联系日趋淡薄,平心而论,我似乎从来没有热爱过那片土地,想起它,更多的是嗟怨与恐惧,我对土地的记忆停留在少年时期,尽管那是这个民族遭逢劫难生灵凋敝的荒唐而又苦难的岁月,但是我这种心理好像还是很离经叛道,数典忘祖,常常令我惶惑忐忑,惴惴不安。为着矫正自己的情感偏执,修复内心的平静坦荡,以求自安,我需要再一次亲近故乡的土地,我甚至应该捧起一把泥土,深嗅、亲吻甚或咀嚼它,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洗刷我的愧疚之感。
回到了故乡,我以为,我会酣饮乡风,我会沉醉乡情,我会感泣故土之爱,我会纾解负疚之心;我以为我会迷失在故乡的空气里,我以为故乡那天然的温情和伦理会把我的灵魂融化,一点一滴渗透到层层泥土之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或许,我的灵魂没有与肉体同时回到故乡,又或者,我从来就没有今后也很难理解故乡,特别是故乡的土地。
这种感觉与我踏进故乡第一眼所见密切相关。第一眼,我看到了什么?土地,当然是故乡的土地。虽然小时候我无数次与它亲密接触,无间无隙,甚至可以说,我的生命就是从那泥土中钻出来的,然而,你要问那是怎样的泥土,我似乎还是无以言述。它不像西北的黄土地,那种黄为一个民族的皮肤着色,神圣而高贵;也不像东北的黑土地,那种黑象征着丰饶和富足,满溢着大地的恩惠:它们都可以凝聚一种情结,激荡一种情怀。家乡的土地黄得不纯粹也黑得不浓郁,它是那种灰不溜秋的颜色,既不能刺激你的视觉,也很难柔软你的内心,它十分中庸,谈不上肥沃还是贫瘠,也说不出荒凉还是温暖,我总是觉得它虽然孕育了生命,但似乎对那些生命并不在意,漠不关心。
对于我的祖辈父辈而言,故乡的土地既是他们的安身之托,也是他们的囚禁之牢。故乡的土地饲养了他们一辈子,也压榨了他们一辈子,欺凌了他们一辈子。
自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生命就牢牢的钉在了灰色的泥土之上,人生际遇就完全被这大地操控。他们就像田野边的一棵树,风儿可以舞动它的枝叶,却无法挪动它的根基,他们的生命属于脚下冷漠的土地,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最后凋零于斯,悄无声息,而大地却无动于衷,缄默如铁。可以说,他们就是一棵棵行走的大树、小树或者病树,永远也无法摆脱土地对他们的身体的羁绊和灵魂的禁锢,他们的喜怒哀乐全都发端于脚下那沉默的土地,他们的命运也只能在田间地头腾挪跌荡;在这样的人世间,生而为农,艰难稼穑,注定终身都是土地的奴仆。他们是真正的低于尘埃,在尘埃之下劳碌奔波,颠沛辗转,悲凉无助,反复轮回。他们活着,奉土地为神明,他们死了,以土地为归宿,他们把灵魂和肉体全都奉献给了土地,大地回赠给他们佝偻的腰身和皱纹里满含的尘土
,还有那枯草丛中一丘荒冢,斜阳寒鸦,苍凉彻骨。土地赐予了他们一切,也剥夺了他们的一切。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经常叮嘱我,要好好读书,他们说:“多读一点书,以后可以吃清闲饭,哪怕是站柜台也比种田好”,那时,我还在贪玩的年龄,并不太明白他们的意思,也没有真的记住他们的话,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才明白,这真是他们最深刻的人生体会。他们一辈子奔忙在土地之中,他们的汗水、泪水或许还有热血全都洒在了土地之上,却只是演绎了一个蝼蚁般的人生的过程而已,他们把自己的年华和希冀全都埋在土地之中,可是它们没有生根发芽,甚至根本就没有破土。这样的生命历程悲怆凄楚,一辈子沉重的付出,却落得生命的飘然而逝,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一样。
考上县一中以后,我就没有真正用功读书了,因为那时我觉得自己即使考不上大学,也可以回乡做一个乡村教师,可以有一只脚不必陷于泥土之中。可能是运气好,两年以后,我居然也考上了大学,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激动和憧憬,其实那时的我对大学生活一无所知,我之激动,我之憧憬,是因为我确确实实的知道:我终于可以将两只脚都从泥土中拔出,我完全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我可以不必重复祖辈父辈的命运,我不是一棵行走的树,我可以做一朵飘飞的蒲公英。
回到故乡,我真的踏上田野,眼前所见与记忆迥异,以前平畴旷野,良田相属,现在大多已经改成大大小小的鱼塘,以前河岸田埂有高低错落的树木,现在已是光光秃秃,直视无碍。年底了,鱼塘已经清塘,水面上的增氧器停止了运行,一个个都趴在哪里,有气无力的样子。走在鱼塘边,捧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它还是那种灰灰的颜色,有一些坚硬,没有嗅到小时候习惯了的那种土腥气。信步而行,哪儿哪儿都差不多,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说不上有什么触动,扔了手中的泥土,拍了拍手上的泥屑,悻悻而归。
突然想起秦牧的散文《土地》,文中引用了《左传》记载的关于晋文公重耳一个典故:重耳带领一帮亡命贵族仆仆奔驰,途中实在饥饿难忍,向一个老农乞食,老农捧了一把泥土给他们,贵族们感极而泣,郑重的收好泥土,跪谢而去。在我看来,这个典故是可信的,因为他们是“落难”的“贵族”。
讴歌土地的人,肯定不是侍弄土地的人,就好像赞美苦难的人其实远离苦难一样。你要说一个从农村走出的人对土地饱含深情,以至于相思成疾,多少有一些矫情吧?
离开故乡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释怀,因为我觉得自己虽然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是故乡的土地并没有放过我,千里万里,它终将我的灵魂捕捉,它把那阴暗的灰色深深的涂抹在了我的生命之中,成为了我的命运底色。